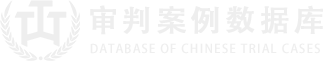裁判要点:
本案均提请一、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其价值在于确立了如下裁判原则:虽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果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本案宣判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座谈会纪要,就该问题与本案持相同立场,故对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此处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时,如何判断某一规范是否属于效力性规范,本案的裁判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法律的空白和漏洞,此处重点阐述该问题。
本案涉及的有众多法条:《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土地承包应当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上述法条均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的后果就是合同无效,给审判实践中适用法律带来较大困难,该案从立法精神出发,虽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集体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将该规范认定为效力性规范,充分保障了集体利益,对于治理当前普遍存在的村、组两级逾越法定程序,防止个别集体成员假借集体名义损害集体成员利益,彰显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公有制本质,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确立了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学理上,本条属于引致条款,其本身不能对法律行为的效力直接产生影响,必须结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予以判断。引致条款不能单独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判断,引致条款引致了公法的规定,是公法进入私法领域的桥梁 ,一些公法得以进入合同领域,从而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同时也带来问题,即究竟哪些公法可以进入私法,如果不加限制就会损害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审判实践中,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1、必须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才能直接导致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才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从而严格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
2、必须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
《合同法》增加强行性规定这一限制,目的是严格区分强行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其约定排除其适用的规范,也即任意性规范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作出约定。所谓强行性规范,是指当事人不得约定进行排除的规范。如果合同违反强行性规范,则有可能被宣告无效。
3、必须是违反了强行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
合同违反强行性规范并不意味着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否定性评价不同,强行性规定可以区分为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取缔规定仅系取缔违法之行为,对违法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并不否认其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效力规定,是指违反该规定,会导致法律行为归于无效。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规定的"应当"、"不得",并非意味着都是效力性规定。一方面,《合同法》上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范围较广,如果不加以限制,直接以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这就可能使大量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从而损害合同自由,有悖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原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公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像躲在木马里的雄兵一样涌进特洛伊城,摇身变成民事规范,私法自治的空间,就在这样一种调整下随着国家管制强度的增减而上下调整。"另一方面,《合同法》中大量强制性规定并没有明确其对合同的影响,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未生效,并不明确。如果一概认定为无效,则不利于鼓励交易,导致财富的浪费。因此,在面对种类繁多的强制性规范,结合立法精神,通过限缩法律条文的文意,使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有所缩小,从而得以针对特定的法律关系。另外,强制性规定的慨念过于宽泛,如果不作限缩解释,当事人就可以选择主张合同有效或者无效,对其有利时主张有效,对其不利时主张无效,从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审判实践中,如何区分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可以区别对待: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该规定属于效力性规范。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如果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也应当将该规范认定为效力性规范。
本案涉及的法律规则之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欠款规定的事项。"从法律规则的结构角度看,对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的分析,法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持两要素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行为模式是指法律规则中为主体如何行为提供标准或准则的范式,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可为模式);应当这样行为(应为模式);不得这样行为(勿为模式)。法律后果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一是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二是否定性法律后果,法律否认某种行为或者禁止某种行为。持三要素的学者认为,任何法律规则具有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要素构成。假定条件指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条件和情况的部分。
无论从两要素说、还是三要素说加以衡量,《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以及本案涉及的其它法条欠缺法律后果要素,即未明确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究竟导致何种法律后果?给适用法律带来困难,难题在于该条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时,如何判断该规范是否属于效力性规范。
本案结合立法精神充分考量,虽然本条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相关规定以后如果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集体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为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理由如下:处分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意愿行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依法属于集体所有的财产共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这种所有权形态下,本集体成员的权利主要是通过成员权来实现的,其所有权主体是单一的,即本集体成员组成的集体。农民集体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虽然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但每一成员不是所有权的主体,不能单独行使所有权,也无权擅自处分集体财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内涵是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对事关集体利益的问题,必须设置一个能够充分反映本集体成员共同意志的程序,以彰显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公有制本质,这对于防止个别集体成员假借集体名义损害集体成员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民主议定程序,《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实体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程序性问题,立法上较为罕见。主要考虑:规定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的事项范围,实际上就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行使的程序进行规定,这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正确行使尤其是本集体成员合法权利的保障至关重要。
应注意的问题。
该案引起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良好反响,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对规制当前农村村、组干部两级依法行使权力,对农村政治稳定具有深远意义,这与我国的历史政治传统、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关。
我国素有"政不下郡县"的政治传统,法律也在县一级止步,留给了农村自治以很大的空间。而村、组两级干部处于沟通"官"与"民"的中介,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乡土问题高度重视,北宋宰相王安石倡导的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创造了保甲制,以乡村精英及家族势力为代表的保甲制,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支撑着王朝的统治,承担着化解纠纷以及部分原本应当由官府承担的职责,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成为官与民之间的减震器、连通器。民国时期,保甲制却完全用于征兵征税,沦为压榨民间暴力的工具,加速了国民党基层权力品质的溃烂,教训不可谓不深。
中国共产党发动更多的民众建立一个最大可能的社会基础,保证了党的影响能够持久地深入农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对村民自治发挥了良好作用,但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农村村、组两级干部在利益的驱动下有法不依,乱作为,侵害农村集体成员利益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地方还因此引发群体性事件,为种种弊端埋下了隐患。
合同的效力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发挥审判职能,站在政治稳定的国家层面高度,正确认定合同效力,对农村村、组干部依法行使权力起到评价、指引作用,防止个别人侵害集体利益,以稳定农村形势。
编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