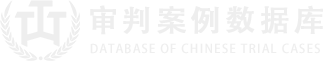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292号民事判决书 /
2008-09-08
裁判要点:
本案审理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1.票据遗失的举证责任应如何分配?民生银行认为,连续的背书记载足以证明系争汇票并未遗失;檀溪公司则认为,对于系争汇票的遗失很难举证,口头的陈述即足以认定。在除权判决当中,法院依据檀溪公司的口头陈述即确认了系争汇票的遗失。而在本案中,法院并未接受檀溪公司的口头陈述,对系争汇票的遗失未予认定。法院在不同的诉讼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存在差别的:
第一,在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阶段,由于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法院只能单方面采信檀溪公司的陈述。票据是否遗失以及票据记载内容的真实性都基本上取决于檀溪公司的自律与诚信。在这一阶段,考虑到举证上的实际困难,法院直接依据檀溪公司的陈述认定票据遗失是适当的。
第二,在申请撤销除权判决诉讼当中,檀溪公司应当被苛以更为严格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不仅应当考虑举证的困难程度,更应当考虑造成举证困难的原因。即使票据遗失属实,檀溪公司对于如此重要物品保管不善也存在着重大过失,要求其在由此引发的诉讼当中承担举证责任并不为过,否则对于持票人而言就显得过于苛刻。从客观方面来看,票据遗失与正常的出票行为具有相同的结果,即出票人丧失了对票据的控制。唯一不同的是,出票人在主观上是否愿意将票据投入流通。对此,民生银行等通过连续背书取得系争汇票的持票人是无法知悉的。本案中,民生银行已经通过出示票据上连续的背书记载证明了系争汇票处于正常的流转之中,应当视为已经完成了票据并未遗失的举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票据遗失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由檀溪公司承担。
第三,在撤销除权判决诉讼当中,要求民生银行就檀溪公司是否遗失票据举证,将不当地扩大民生银行的举证范围。根据票据法理论,民生银行对基础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仅限于与其直接前手之间,法院不能苛求持票人对每一个票据流通环节的合法性与真实性都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法院依法追加了民生银行的直接前手傲尔公司,并查明了傲尔公司向民生银行质押票据的事实。据此,应当认为民生银行已经完成了对票据基础关系的证明责任。
综上所述,为了保护持票人的正当权利,避免票据债务人在票据正常流转后谎称票据遗失的情况发生,法院认为,在撤销除权判决案件当中,票据上的背书记载情况应当比票据遗失的口头陈述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在持票人出具连续背书票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推定票据处于正常的流转当中,除非主张票据遗失者能够提供足够的相反证据。
2.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应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据此,只有系争汇票的最后持有人才有资格申请公示催告并要求除权判决。
民生银行认为,系争汇票并未遗失,不存在最后持有人的问题,檀溪公司无权申请公示催告。同时,即使系争汇票确实遗失,檀溪公司也不是最后持有人;檀溪公司认为,在系争汇票遗失之前,其实际保管着系争汇票,因此是最后持有人。
法院认为,无论檀溪公司关于系争汇票遗失的陈述是否属实,其都并非最后持有人。《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背书连续,是指票据第一次背书转让的背书人是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前次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是后一次背书转让的背书人,依次前后衔接,最后一次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是票据的最后持票人。”据此,最后持有人只能依据系争汇票的记载情况来确定,而不应当依据系争汇票物质形态上的占有情况来确定。根据票据的记载,在票据遗失时的最后一位票据权利人就是最后持有人;仅仅在实物形态上占有票据但依据票据的记载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人不属于最后持有人。
法院认为,关于最后持有人的判断也可以借助对立法目的的解读进行。法律规定只有最后持有人才有权申请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的原因在于,最后持有人与系争汇票的流转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不借助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等公权力的行使,就可能因为票据的流转而承担不应当承担的票据责任。根据立法的意图,只有可能承担不当票据责任的人才能成为最后持有人。仅仅在物质形态上占有票据但依照票据的记载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人并不会由于票据流转而承担不当的票据责任,因此不应成为最后持有人。本案中,法院已经认定系争汇票并未遗失,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最后持有人。同时,即使系争汇票确实遗失,檀溪公司也不是最后持有人。依据檀溪公司的陈述,在系争汇票遗失前,其已经完成了出票行为,收款人京伟公司已经在第一背书人处加盖了印章。在这种情况下,系争汇票的遗失只会给京伟公司而非檀溪公司造成损害。京伟公司将票据返还给檀溪公司的行为,并不能使得檀溪公司成为最后持有人。
3.正当理由应如何认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民生银行未在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存在严重分歧:檀溪公司认为,民生银行未在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不具有正当理由,无权起诉要求撤销除权判决;民生银行则认为,法院的除权判决刊登于《人民法院报》之上,其作为金融机构,并没有订阅该报纸,因此没有及时获悉公示催告等信息,未在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具有正当理由。
法院认为,民生银行未在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具有正当理由。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民生银行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履行了必要的审查手续,不存在过错。民生银行在收到傲尔公司的票据质押贷款申请后,对票据的真实性进行了鉴定,并向付款行农业银行发函进行了查询,在得到明确答复后才接受了系争汇票的质押。《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立法意图在于,督促利害关系人及时行使权利,不要成为“权利上的睡眠者”,否则可能因自身的懈怠而丧失诉权。本案中,民生银行已经尽到了金融机构从事票据质押业务时所应当尽到的勤勉义务,其诉权因此不应受到上述条文的影响;另一方面,檀溪公司对于诉讼的发生具有过错。本案中,檀溪公司在隐瞒系争汇票已经背书转让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公示催告并进而要求法院作出除权判决,这些行为使得民生银行无法就系争汇票行使质权。可以说,民生银行是因为檀溪公司的不当行为而被动地卷入到诉讼当中。综上所述,对于正当理由应当从宽把握,只要檀溪公司不能证明民生银行在行使权利方面存在懈怠就应当推定正当理由的成立。
法院认为,将当事人的过错情况作为正当理由是否成立的判断依据是恰当的。这样既有利于防止票据债务人通过伪报票据遗失来侵害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也有利于敦促票据债权人在从事票据行为时尽到必要的谨慎义务。
最后,关于正当理由的认定,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金融机构未订阅《人民法院报》这一事实本身是否构成正当理由。法院认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构成正当理由。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及时了解公告信息是金融机构应尽的勤勉义务之一。保持信息畅通既有利于对金融机构自身利益的维护,也有利于对客户利益的保障。金融机构应当对司法实践当中与其利益相关的常态化做法具有基本的了解,而《人民法院报》上所发布的公告信息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金融机构不注意收集相关信息、闭门搞业务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检索公告信息所产生的费用,理应视为金融机构开展经营活动所应当承担的必要成本。其次,通过公告传递信息应当坚持对等原则。金融机构通过《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发布债权转让或催收信息的做法并不鲜见。金融机构在将媒体作为信息发出渠道的同时,也理应将其作为接收渠道,否则对非金融机构的当事人将明显有失公允。再次,公告送达是司法活动所必需的“下下之策”,尽管有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公告送达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许多司法程序将根本无法进行。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法律为公告送达设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法院只有在穷尽了其他的方式而仍然无法完成送达时方可采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告送达是由于整个社会诚信缺失所徒增的诉讼成本,每一位诉讼当事人都必须承担,金融机构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