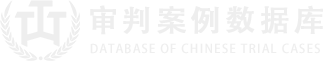裁判要点:
本案属于航空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南航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免责事由,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具体涉及到以下三个问题:一、本案是否适用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二、宠物死亡后的价值确定;三、饲养人就宠物死亡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一、本案是否适用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
损害赔偿限额一般在特殊侵权法中适用,是对损害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赔偿限额,即不按照实际损失全部赔偿,是对全部赔偿原则的修正与衡平。基于航空运输的特殊性及其本身存在的风险,各国均采取了赔偿限额制度。我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也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为此,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于2006年1月发布了《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根据该规定,"对旅客托运的行李和对运输的货物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公斤人民币100元。"故在本案中,某航空公司主张按照上述标准赔偿赵某3800元。
然而,损害赔偿限额也有例外规则,《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经证明,航空运输中的损失是由于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无权援用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有关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证明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有此种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还应当证明该受雇人、代理人是在受雇、代理范围内行事。"上述规定突破了责任限额。本案中,某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对承运的货物应当精心组织装卸作业,轻拿轻放,严格按照货物包装上的储运指示标志作业,防止货物损坏。然而,某航空公司委托的空港地服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卸车过程中,明知航空箱内装有活体动物,却未尽到合理地谨慎注意义务,未采用适合的装卸工具和装卸方式搬运货箱,而是由单人将航空箱直接从托车上推至地面,导致航空箱落地时侧倒,金毛犬因此受到惊吓,从航空箱底部破损处挣扎后逃逸,金毛犬逃逸后死亡与搬运中的不当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空港地服公司作为专业的地面服务公司,受南航公司委托为其提供行李装卸服务已近20年,其装卸人员应当知道其轻率地装卸行为可能导致货箱受损、活体动物受惊,故本案符合《民用航空法》有关赔偿责任限制的例外性规定,南航公司在本案中不能适用《民用航空法》有关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对上述不当装卸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裁量。
二、关于宠物死亡后价值的确定问题。
关于动物价值的认定,非宠物类动物较少有争议,或按实际支出治疗费用,或按同类品种动物的市场价格既定。宠物类动物受损价值之所以难以确定,一是市场因素较为复杂,宠物的交易价格一般没有规范的市场指导价,任意定价的情况较为普遍;二是无相应的鉴定评估机构可行评估,在法院登记入册的评估机构中无一家有资质可对宠物价值进行评估,如寻找名册外评估机构咨询、评估,则必须考虑成本支出及风险问题;三是宠物的附着价值或可增值部分损失难以确定,如血统、年龄、与饲养人的感情等。基于上述因素,死亡犬只的价值大多只能由法院依职权调查所得的"诚实价格"而定,但如遇到特别名贵而价值较大的宠物受损案件,应当寻求特别询价途径加以解决。
本案中,赵某从金毛犬幼时起开始饲养,故金毛犬的死亡给赵某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应包括其初始购买价格及必要的饲养成本。由于目前尚无对饲养犬只的价值进行评估及确认的机构,法院经过市场调查测算,根据同类犬只的市场价格,结合涉案金毛犬的品种、年龄、饲养期限,酌定金毛犬死亡时的损失金额是合理的。
三、饲养人就宠物死亡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是指精神利益损害,又可称非财产利益损害。而精神损害赔偿又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权利或人格利益受到侵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从上述概念来分析,以及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来看,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下列特征:客观上表现为不法行为造成非财产损害或精神损害;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在法律适用上以法律规定为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四条规定:"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审判实践中,对于饲养人就宠物死亡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只能严格适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宠物不具有人格权利或人格权益的属性,并非"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之范畴,因此不应支持精神损害索赔主张。
另一种意见认为,宠物之"宠"即代表一定的精神属性,不仅具备感情成份,亦可窥见饲养人之心血,甚至为部分人的感情寄托,不可抹杀宠物所具有的有生命、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性,仅仅按照宠物所显价格给予赔偿,难以弥补其精神方面受到的损害,因此可考虑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即宠物受伤害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可在特定条件下考虑,但需严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以法律规定的范围为限,不宜作随意性扩大。一般情况下,宠物并不能作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它仅是饲养人感情中较为重视的有生命的财物,而无论这种感情有多深厚,都不能间接肯定感情超越亲人的现象。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宠物上升为具有精神属性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从而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因此,对宠物是否在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内应当进行分析。作为宠物要上升为有精神属性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应当从人对宠物所寄予的感情和依托宠物所形成的人格利益来分析确认。同时,构成精神损害赔偿,还需满足以下条件:1.侵权人系故意或重大过失,并因这种故意、重大过失造成损害后果;2.有证据证明饲养人的精神痛苦十分严重。另外,在对宠物受损时饲养人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额上,必须考虑人之侵权受损时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界定,不宜出现过高的赔偿金额。
本案中,某航空公司委托的空港地服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卸车过程中,未采用适合的装卸工具和装卸方式搬运货箱,其行为显然存在重大过失,且金毛犬逃逸后死亡与搬运中的不当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金毛犬系赵某夫妇从幼时起开始喂养,朝夕相伴已逾三年,从本案的证据看,金毛犬已成为赵某夫妇的"伴侣型"宠物,超越了一般动物与主人之间的关系界限,其被赵某视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具有特定性和不可替代性,金毛犬因托运装卸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致死,给赵某夫妇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综合上述情况,为抚慰当事人的精神创伤,以及对不当装卸行为的惩戒,法院酌情支持了赵某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