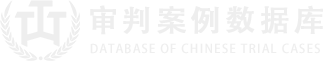裁判要点:
本案相对于同类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时间跨度长、主体多元化、双方无过错,导致事实难认定,实体难处理。如何理解和适用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解决下列四个问题,是本案正确判决的关键。
1.如何确定本案纠纷的性质。
本案中,由于医疗机构不是冻干血浆的生产者,且当年输入患者(原告)体内的冻干血浆已不存在,这就使得本案的处理不同于一般的医疗损害纠纷。为查清事实,必须依法追加销售者,以查明和追加生产者参加诉讼。多个不同身份的被告的出现,使得本案诉讼主体间法律关系复杂化。对于本案的定性,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为产品责任纠纷;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本案判决采纳了第三种意见。
首先,医疗机构向住院患者提供药品的行为,是医疗行为,不是买卖行为。住院患者使用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与门诊病人持处方自行向药房或药店买药,虽然患者都支付了对价,但区别明显,表现在:一是性质不同,住院患者接受和使用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是医疗合同的附随义务,未经医疗机构同意,患者是不能自行购买、使用药品的;门诊患者在医疗机构开出处方后,医疗合同即已履行完毕,医疗机构对患者何时购药、向谁购药、购买何厂家生产的药品并无要求。二是目的不同,医疗机构为住院患者提供药品,虽然药品本身也产生经济效益,但其根本目的是为医疗服务,追求的是医疗利润;药房或药店售药给患者,目的是为销售药品,追求的是销售利润,患者要买什么药就卖什么药。三是后果不同,住院患者因使用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承担的是医疗责任,而门诊患者自行购药使用造成损害的,医药机构(药房)或药店承担的是产品责任。
其次,住院患者因医疗机构使用药品受到损害的,其与药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产品质量责任关系。消费分为生产和生活两大类,在因生产消费引发的诉讼中,生产者作为利害关系方,可申请参加诉讼,也可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身份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而在因生活消费引发的诉讼中,受害人无论是否消费者,只要因投入流通的产费引发的诉讼中,受害人无论是否消费者,只要因投入流通的产品受到损害,均可选择直接向生产者求偿,双方之间形成直接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医疗消费属于生活消费,住院患者因医疗机构输注冻干血浆受到损害,其与生产者之间形成产品质量责任关系。
再次,多种责任混同产生一个损害后果,应当按责任大类定性。根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消费者起诉时往往将销售者和生产者列为共同被告,但在产品责任查清后,法院只能判决生产者或销售者中的一方承担责任,不能判决两方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有其特殊性,医疗机构不是瑕疵冻干血浆的生产者,其主观上无过错,瑕疵冻干血浆的生产者具备免责事由,原告的损害是由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共同造成的,损失单独由医疗机构或生产者承担都不公平,应当由两方共同分担受害人的损失。医疗损害与产品质量损害都属于人身损害范畴,故本案性质应定为人身损害纠纷。
2.谁对“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
输入冻干血浆与患丙肝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是确定本案侵权事实是否存在的关键。与此相关的不争事实有三点:一是丙肝传播途径以血源性感染为主,但还存在吸毒、针头或器械划伤、不洁性行为等多种其他感染途径;二是当时国内医务界对丙肝尚缺乏认识,医疗机构不具有检测患者体内是否携带丙肝抗体的能力和条件;三是原告出院后至被确诊患丙肝相隔6年。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最终确信,是依法定程序在对当事人所举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官在受害人与医疗机构之间如何分配证明责任,是本案程序处理的难点,也是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
本案的审理,没有简单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将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直接推给医疗机构,而是首先要求受害人对其主张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承担证明责任,在此基础上,要求医疗机构对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与其说是举证责任倒置,不如说是举证责任转移,这一做法彰显了司法公平。首先,本案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可能通过鉴定确认因果关系,要求医疗机构直接证明患者出院6年后新确诊的疾病与6年前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确有不公平之处,客观上存在谁举证、谁倒霉之可能。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医疗机构对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照此规定,作为提出主张存在因果关系的原告,也应当就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首先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要求医疗机构对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为何对另一被告即生产者不作如此要求呢?从感觉上讲,冻干血浆的生产者相对于医疗机构,似乎更应该承担其产品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之所以未要求生产者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是因为按照举证责任的实质性分配标准,举证责任应当由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产品进入流通渠道后,生产者脱离了对产品的控制,他人所受损害是否由该产品造成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产品的使用人或受害人最了解,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产品的使用人或受害人。本案中,冻干血浆的控制者与使用者都是医疗机构,故由医疗机构承担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义务,更显公平。
至于原告住院时体内是否携带丙肝病毒,或在出院后是否因其他途径感染丙肝病毒,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据规则,这一证明责任应当由提出主张的被告承担,要求原告自己证明自己是荒唐的。在原告提供卫生部门的通知以及权威教科书的相关说明后,应当认定原告完成了证明义务,此时举证责任自然转移给医疗机构,由于其不能证明其医疗行为与原告患丙肝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推定存在因果关系是正确的。即使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的判断标准,也能得出这一结论。
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限。
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距输注冻干血浆之日已逾14年,距被确诊患丙肝已逾7年,距知道致病原因近10年,其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这是本案双方争议的又一个焦点,也是本案处理的难点,分析这一问题,应当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医疗侵权的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产品责任的诉讼时效适用《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考量原告之请求是否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需要区分三个时间标准,即:输注冻干血浆的时间、确诊患丙肝的时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致病原因的时间。原告1991年11月接受医疗机构输注冻干血浆,其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冻干血浆携带丙肝病毒的情形,因而不知道权利被侵害;1997年原告虽被确诊患丙肝,但由于缺少专业知识,不知道致病原因,也就不知道权利被侵害,无法主张权利;2003年11月原告收看电视知道致病原因,由此时应推定原告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此时虽距确诊患丙肝已7年之久,但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致害人尚未超过一年,故其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间。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该法条中“十年”是最长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或者其他?值得研究。毫无疑问,如果是最长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则原告之请求要么超过诉讼时效,要么实体权利已灭失。该法条由两款组成,结合第一款的规定来看,第二款中的“十年”似乎是最长诉讼时效。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产品质量法条文释义》对该法条的解释,也认为“十年”是指最长诉讼时效。但是,仔细分析,这里的“十年”并不同于最长诉讼时效。首先,该条第一款中的“诉讼时效”与第二款中的“赔偿请求权”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权利的保护期间,后者则是一项请求权利。其次,起算日不同,最长诉讼时效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也即请求权的取得之日起算,而这里的满十年丧失的赔偿请求权则是从产品交付之日起算。“交付”是指物的转移占有,侵权则是指占有物对占有人造成的损害,两者的性质不同,交付时不一定是侵权时,无侵权也就不存在赔偿请求权,无赔偿请求权也就谈不上诉讼时效的保护。显然,这里的“十年”不是最长诉讼时效。那么是否除斥期间呢?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于法定存续期间届满而当然消灭的期间。该法条第二款表述“赔偿请求权自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似乎就是除斥期间,其实不然。除斥期间,预定的是某种权利的存续期间,自权利成立时起算。而这里的“十年”,是从产品交付之日起算,同上道理,交付后不一定发生侵权,没有侵权也就不可能有赔偿请求权的产生,请求权的存续也就无从谈起。产品缺陷的表露时间、致人损害的时间、受害人知道损害原因的时间、受害人主张权处的时间,并不都是一致的,后者往往滞后于前者。显然,这里的“十年”无论是作为最长诉讼时效来理解,还是作为除斥期来理解,都是不恰当的。那么,“十年”的含义到底指什么期间呢?本案的判决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释,“十年”是对受到安全使用期不超过十年的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规定。简言之,“十年”是赔偿请求权的取得期间。只要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时间,发生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后的十年内,受害人即享有赔偿请求权,至于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当事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后的二年内主张权利,其权利都应当得到保护。但在交付满十年后,即使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失,受害人也不享有赔偿请求权,除非尚未超过产品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由此解释,本案难点迎刃而解。原告是在1991年输注(交付)冻干血浆当日感染丙肝病毒,按理原告也就在当日取得赔偿请求权,但是由于病毒未发作对原告未产生实质损害,原告不知情也不知被侵害,赔偿请求权的实际取得只能从1997年其被确诊患丙肝之日起算,又由于其不知道致病原因和致害人,其虽取得赔偿请求权,但却无法主张权利。按照时效理论,诉讼时效应从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人之日起算。十年后的2003年11月,原告收看电视知道致病原因,其在2004年9月6日行使赔偿请求权(提起诉讼)未超过该法条第一款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故其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间。
4.免除生产者的无过错赔偿责任,能否依据公平原则让其分担受害人之损失?
如前所述,本案存在着医疗侵权与产品侵权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归责,后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医疗机构主观上无过错,于法不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因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适用公平原则让其分担受害人的损失。这一点易于理解和接受。而生产者该不该赔偿或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则存在着法律障碍。《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根据这一规定,应当免除生产者的赔偿责任。那么,能否适用公平原则判令生产者分担受害人之损失呢?这是本案实体处理适用法律的又一难点,值得研究。
产品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它不以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为构成要件,只要产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或生产者具备法定免责事由,否则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学者们普遍认为:无过错责任是法律为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弱者利益,对于一些特殊业务活动造成的特殊损害规定的责任,而公平责任则是法律为弥补过错责任之不足,所设立的一种责任。因而,公平责任仅适用于按照过错原则处理又显失公平的情况,不适用于法律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按照这一理论,本案既然依法免除了生产者的无过错赔偿责任,就不能再适用公平原则要求生产者分担受害人的损失。照此推论,生产者依据该法条免责的全部损失,只能由受害人独自承担。这一结果是否公平,无须职业法官依据职业能力评价,一般公众仅凭良知亦能得出结论。结论与理论似乎开了一个玩笑,旨在体现社会公平、保护弱者利益而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没有能保护弱者(消费者),反倒保护了强者(生产者)。以本案为例,即使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受害人得不到赔偿,尚且可以适用公平原则得到补偿,而适用无过错责任,作为弱者的受害人却得不到补偿,岂非憾事!立法在这里又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和否定无过错责任原则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这一原则充分保护了弱者的利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和否定相关免责事由的合理性,免责事由确实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和研究。但是,仅凭本案实例,我们有理由怀疑公平原则不能作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补充适用的理论的合理性。
基于以上认识,本案判决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突破上述理念的束缚,适用公平原则让生产者分担部分损失,既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