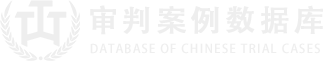裁判要点: 共同海损制度是传统海商法中最古老的制度之一,是“一人为大家作出的牺牲由大家分摊”的“同舟共济”精神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现形式。近半个世纪以来,因共同海损理算的耗时、繁琐而使该制度的存废取舍渐次受到现代效率型社会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但即便如此,各国海商法还是概莫能外地肯定、张扬了该制度所蕴含的公平之法价值,而将效率、效益价值放在了次要位置。申言之,共同海损制度仍然是现代各国海商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国海商法亦设专章即第十章规定了共同海损的有关问题。本案即是较为典型的共同海损分摊纠纷案件,涉及共同海损的构成条件、引发共同海损的原因的法律定性、不可免责过失所致的共同海损是否可以拒绝分摊等诸多海商法领域的专业性问题,且一些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达成普遍性共识。在本案判决中,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合乎理性和合乎法律规范的解决,因而极具代表性。 1.有关拖带费等费用支出是否构成共同海损。依通说,构成共同海损的条件是:船、货面临共同危险;措施须有意合理和有效果;牺牲和费用须为共损措施的直接合理后果,且是特殊的、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的。这与我国《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共同海损,是指在同一海上航程中,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遭遇共同危险,为了共同安全,有意地合理地采取措施所直接造成的特殊牺牲、支付的特殊费用”的规定是吻合的。“琴海108”轮因主机故障而漂航,船货面临共同危险,此时雇请拖轮拖至避难港越南金兰湾的拖带费属共同海损费用,对此并无争议。问题是,在金兰湾港是否意味着船、货已经获得了安全?可以肯定的是,在避难港,船、货在物理意义上是安全的。但是,从商业意义上讲,由于主机故障基于客观原因不能排除、船舶没有继续航行的能力,不能自行航行至目的港,致船、货均无法实现其本航次的商业目的,故即便在避难港,船、货仍然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商业意义上的危险。亦即在此问题上,共同利益派的观点较之共同安全派的主张更符合共同海损制度的本质性要求。解决此商业意义上的危险,航运习惯有两种做法:一是船货方签订“不分离协议”(Non-separation Agreement)后,将货物换装它船运往目的港;二是雇请拖轮将船舶及货物一并拖往目的港。第一种方法所发生的转运费,如果低于由原船舶将货物运往目的港的费用,或者低于第二种方法所发生的费用,则该转运费可作为替代费用,列入共同海损进行分摊,否则不得作为替代费用要求分摊。被告抗辩称货物换装船舶所发生的转运费低于自避难港至目的港的拖带费,故该程拖带费用因加大了共损牺牲而不能列入共同海损。这一抗辩倘若有证据的支撑,则当然应得到法庭的支持,但是,由于该抗辩主张仅限于推测,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故不足采信。法庭认定自避难港至目的港的拖带费用是“有意的和基本合理的”,是解决船、货面临的共同商业风险所必须的,这一认定以已有的证据为基础且不悖于航运习惯,具有公正合理性,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合乎共同海损制度所倡导的公平原则或者说公平理念,故这一认定无疑是正确的。 2.对引发共同海损的直接原因的法律定性。这里的所谓法律定性,是指要依法确定引发共同海损的直接原因是属于意外事故、还是属于承运人可免责或不可免责的过失。原被告均认可引发共同海损的直接原因是:主机各缸的空气启动阀启动活塞密封环失去弹性、气密较差,加之第七缸空气启动阀阀盘断裂,该缸完全失去气密,导致进入各缸的启动空气压力不足而无法启动主机。对此原因进行法律定性,涉及如下两个问题:开航前和开航当时船舶主机是否已经存在此缺陷?若已存在,那么此缺陷是否属于潜在缺陷?“琴海108”轮主机全部九个缸的密封环均失去弹性、气密较差,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常识告诉我们,除非人为地使密封环失去弹性,否则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期间和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该期间肯定远远超过船舶1999年3月25日开航至4月4日主机故障的10天时间,即不可能在10天之内九个缸的密封环均由良好弹性变成了失去弹性。换而言之,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密封环失去弹性的缺陷即已客观存在,从而排除了意外事故引发共同海损的可能性。那么,该缺陷是否属于承运人可免责的过失?这取决于密封环失去弹性这一缺陷的属性,即是否属于潜在缺陷。海商法上的潜在缺陷,是指谨慎的或勤勉的专业人员以通常方法检查船舶所不能发现的缺陷,法律并不要求检查船舶时特别地谨慎或特别地勤勉。在航运实务中,检查船舶是否适航,的确无必要每次都打开主机的九个缸以确认密封环是否老化和气密,倘若仅有部分密封环老化失去弹性,将其认定为潜在缺陷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所有密封环均已老化失去弹性,则是谨慎专业人员检查船舶时应当发现的,否则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船舶就毫无意义,“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的法律规定将形同虚设。故而符合逻辑的结论只能是:主机密封环均已老化失去弹性的缺陷并非潜在缺陷,而是不可免责过失所致的开航前或开航当时的船舶不适航,且在航行途中必然性地导致了共同海损的牺牲或费用。 3.不可免责过失所致的共同海损,非过失方可否拒绝分摊。对此国际社会曾有三种做法:第一,1974年北京理算规则规定,不可免责过失所致的案件,不进行共同海损理算,但可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协商另作适当处理(1994年北京理算规则已对该规定作了修改)。第二,美国法院一度主张,对驾驶疏忽等过失,船东可免责,但不能再请求货方分摊共同海损,即船东必须没有过失才能请求共同海损分摊(杰森条款、新杰森条款对此做法予以了修正)。第三,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的规定,即本案所涉及的问题。 案涉提单的背面条款有“共同海损应根据承运人的选择在任何港口或地点根据197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理算”的规定,该规则中的规则D规定:“即使引起牺牲或费用的事故可能是由于航程中一方的过失造成,亦不影响在共同海损中进行分摊的权利;但这不应妨碍就此项过失向过失方可能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或该过失方可能具有的任何抗辩。”我国《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与上述规则D如出一辙。对此规定有一种所谓“先分摊后追偿”的解释,认为即便承运人不可免责过失所致的共同海损,受益方也应予以分摊,然后再向过失方追偿。显然,这种解释的错误在于把“引起牺牲或费用的事故可能是由于航程中一方的过失造成”这一不确定的状态确定化了,以致得出不可免责过失所致的损失亦可转嫁他人的结论。另外,损失转嫁他人后又反过来向过失方追偿,岂不多此一举?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分摊或直接要求过失方赔偿? 实际上,上述规定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共同海损成立及理算与共同海损分摊是两个层面或两个阶段的问题,不可彼此混淆。只要符合上文所述的共同海损成立条件,即可宣布共同海损并请求理算,此时并不考虑对引发共同海损的直接原因的法律定性,即不考虑是意外事故还是承运人可免责或不可免责过失引发共同海损。然而,当进入共同海损分摊阶段时,则面临如下两种不同的情况并应作出不同的处理:第一,暂时不能对引发共同海损的直接原因进行法律定性,即暂不能确定是意外事故还是承运人可免责或不可免责过失导致共同海损,则受益人须先分摊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待查清系承运人不可免责过失致共同海损后,再就分摊金额向承运人追偿。第二,业已查清共同海损系承运人不可免责过失所致的,有关损失理当由承运人自行承担,这是承运人违反法定最低责任的必然结果,受益人可以拒绝分摊这种损失。本案即属后一种情况,故法院判决支持被告拒绝分摊共同海损的请求无疑是合乎法律旨意的。当然,承运人虽不能从受益人处获得分摊,其宣布共同海损并进行理算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即承运人对拒绝分摊的部分可向船东保赔协会要求赔偿。
商务咨询:
010-62515610(机构用户)
010-62514898(个人用户)